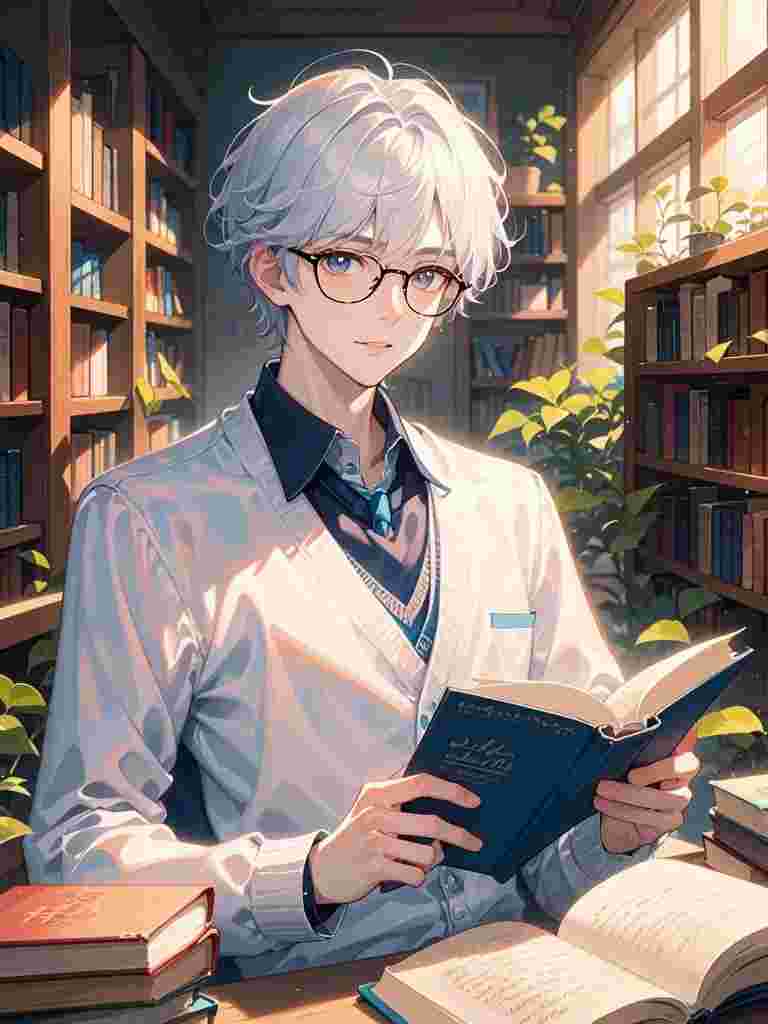第4章 槐树开花前的“葬礼账”
苏晚昭捏着那张匿名信在账房坐到天亮。
烛芯爆了三次,她就拨三次,目光始终锁在“三日后,槐树开花七个字上——老槐树在后山坟场,她来绣楼七年,从未见它开过花。
“在想槐树?
沈青竹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
他手里端着粗陶碗,药香混着热粥气扑进来。
苏晚昭这才发现天己大亮,窗外麻雀正啄食青石板上的米粒。
“曼陀罗药粉的事。
沈青竹把碗推到她手边,“我昨日跑遍药铺,苏州城只有城南纸扎铺会批量买。
纸人纸马要防虫蛀,他们常拿曼陀罗泡浆糊。
苏晚昭把信往袖中一塞,抄起算盘就往外走“去纸扎铺。
城南纸扎铺挂着褪色的白幡。
赵西娘正蹲在门槛边剪金箔,见是绣楼的人,手里的剪刀“当啷掉在地上。
“买纸钱?
她搓着沾金粉的手,笑得比纸人还假,“您说要多少,我这就——要查的不是纸钱。
苏晚昭把算盘往柜台一磕,“赵老板,林夫人弟弟的棺材铺,上个月是不是给你送了三车柏木板?
赵西娘的笑僵在脸上。
她往门外张望一眼,突然拽着苏晚昭的袖子往里间拖。
沈青竹站在门口,指尖轻轻叩了叩门框——这是他们约好的“有动静就出声。
“七年前开始,每年正月十五。
赵西娘从柜台底下摸出本油乎乎的账簿,翻到折角那页,“林夫人让她弟弟来订纸扎,说是给小姐‘陪嫁’。
可哪有活人年年给死人送嫁妆的?
苏晚昭凑过去。
泛黄的纸页上,墨迹深浅不一“纸衣七套,头面七副,绣鞋七双纸嫁衣一套,珍珠十二颗,最底下歪歪扭扭签着“林晓棠。
“这名字……她翻出怀里的陪嫁账,李妈记的丫鬟名单正和纸衣数量对得上。
沈青竹俯身看账簿,指节抵着最后一行批注“今年的单子还没填。
“填不了!
赵西娘突然压低声音,“上月底林夫人亲自来的,说‘今年要续补一人’,让我把纸衣尺寸改大两寸。
可她连名字都没留,就说‘到时候自然有人送’……苏晚昭的指甲掐进掌心。
她想起前两日在后院井边,小桃的替换丫鬟阿菊正蹲在地上哭——那丫头身量比小桃高半头,正合“改大两寸。
“走。
她抓起账簿往怀里塞,转身时撞翻了赵西娘的金箔盘。
沈青竹己经摸到门闩,回头时见她眼底烧着团火,像要把这满屋子纸人纸马都烧成灰。
“三日后。
苏晚昭捏紧袖中匿名信,“槐树该开花了。
苏晚昭踹开云绣楼后门时,绣娘们正捧着绷子往堂屋去。
她抓过路过的小丫鬟“李妈呢?
“在后厨筛米!
李妈听见脚步声抬头,筛子“哐当掉在米缸上。
苏晚昭扯着她往柴房走,袖口蹭了墙灰也不管“王婆子最近调人去后院没?
“昨儿个……李妈手指绞着围裙带,指节发白,“她说后花园缺香料,把小翠叫去了。
那丫头才来三个月,连香粉罐子都认不全……苏晚昭转身就走。
李妈追出来,声音抖得像被风吹的槐叶“晚昭姑娘,您可当心些,林夫人昨儿个还问起您查账的事……沈青竹是在月上柳梢头时摸进后院的。
他背着药箱,袖中藏着从医馆顺的银针——说是巡诊看绣娘的冻疮,实则盯着老槐树转了三圈。
树根旁新土松着,踩上去软得反常。
他蹲下身,指甲抠开表层浮土,露出半尺深的坑——坑底铺着香灰,混着没烧尽的黄纸。
“镇魂。
他低声自语。
解下腰间红绳系在树杈上,又掏帕子包了把土。
指尖沾了香灰,在掌心搓出炭渣味儿——和上个月在义庄见的冤魂案,一个路子。
苏晚昭把赵西娘的账本副本塞进账房墙缝时,更漏刚敲过三更。
夹层是她用算盘珠磨了半月抠出来的,连林夫人都不知道。
她拍了拍砖缝,转身看见窗台上多了滴水——窗明明闩得死紧。
雨是后半夜下的。
炸雷劈开天幕那刻,苏晚昭从竹榻上惊起。
烛火忽明忽暗,照见桌上多了朵纸槐花——花瓣是金箔剪的,花蕊用的是血点朱砂,和匿名信上的字迹,一模一样。
她抓过纸花冲进雨里。
账房后窗的泥地上,两行鞋印清晰——是林夫人常穿的缠枝莲绣鞋。
“晚昭!
李妈撞开账房门时,苏晚昭正把算盘珠掰得噼啪响。
老妇人鬓发散着,手里攥着半块带泥的帕子“小翠……昨晚就没回来。
我偷偷去后院瞧,老槐树下真开了花!
“什么花?
“纸做的!
李妈把帕子摊开,里面躺着朵蔫了的纸槐花,金箔被夜露泡得发皱,“和您桌上那朵……一个样。
苏晚昭捏着纸花的手紧了又松。
窗外雨还在下,打湿了廊下的灯笼,晕开一片血色。
她望着李妈发抖的嘴角,突然笑了——林夫人越是急,破绽就漏得越多。
“去厨房烧碗姜茶。
她把算盘往怀里一揣,“明儿个,该请官府的人来喝杯茶了。
雨幕里,林夫人的绣楼影子被拉得老长。
二楼雕花窗后,一道身影闪了闪,金镯子碰在窗棂上,叮铃作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