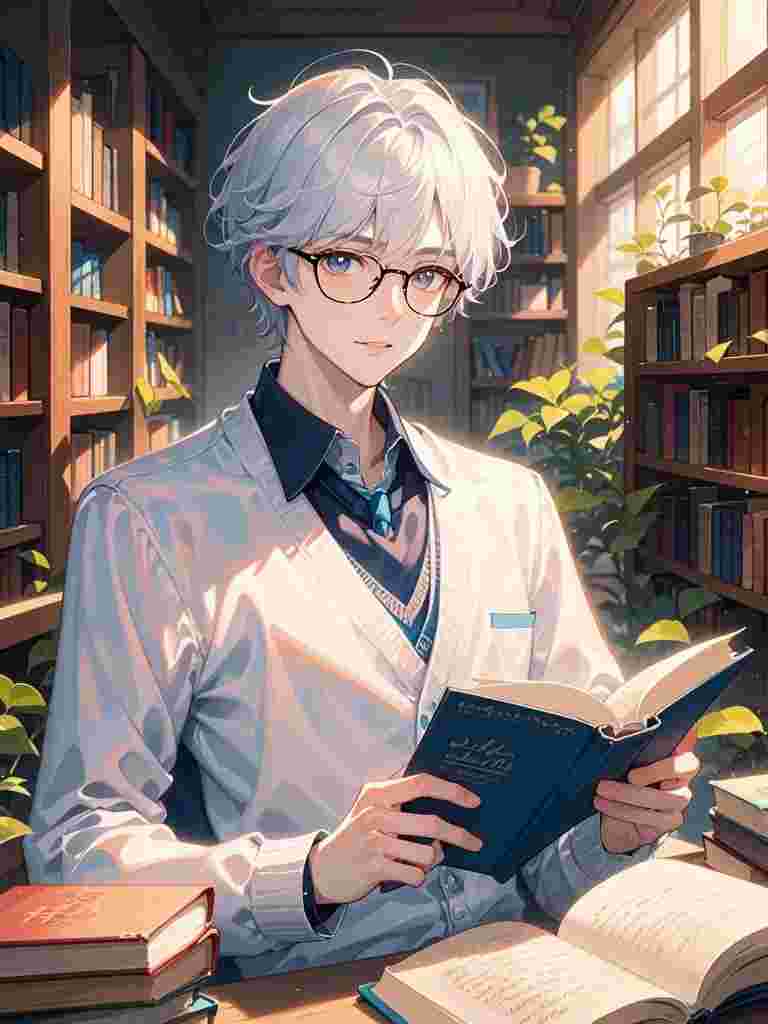第1章 笼中白鹤
霉味是有重量的。
陈年的灰尘裹挟着木屑腐朽的气息,在几道斜射进废弃仓房的光柱里狂乱地浮沉、舞蹈。
每一粒微尘都仿佛带着岁月的粘滞感,争先恐后地试图附着在闯入者的华服上。
朝颜下意识地用宽大的、绣着精致鹤纹的丝绸袖口掩住口鼻,秀美的眉尖紧紧蹙起,形成一个惹人怜惜又透着疏离的弧度。
袖口柔软的丝绸滑过她漆器般光洁细腻的下颌,带来一丝微凉的触感,与这污浊的环境格格不入。
这废弃的堆物之所,弥漫着破败与遗忘的气息,绝非她该踏足的地方。
她是朝颜,吉原游郭名动江户的“白鹤。
她只该属于“琼楼最高处,那间俯瞰着整个吉原灯火、名为“雪见的香阁。
“雪见里没有霉味,只有价比黄金的南海沉香终日缭绕,清冽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腻,丝丝缕缕渗入房间每一寸金箔底纹的唐纸墙壁。
寸锦寸金的吴服,以最繁复的工艺织就西季花鸟或祥云仙鹤,一层层裹着她玲珑有致的身躯,既是华美的包装,亦是沉重的枷锁。
无数贪婪的、附庸风雅的、或探究或占有的目光,如同无形的丝线,将她高高供奉在镀金的、冰冷的高台之上,仰望,觊觎。
她曾是京都名门浅井家的玉兰,闺名清姬。
记忆里,是庭院深深,是墨香与茶韵,是和歌的婉转与汉诗的磅礴。
母亲教导她仪态万方,行走坐卧皆成画;父亲赞她通晓诗书,灵慧通透。
浅井清姬,曾是枝头最矜贵的那朵玉兰,沐浴着门庭的荣光。
然而,政治倾轧的风暴席卷而来,毫无预兆。
一夜之间,朱门崩塌,巨厦倾颓。
悬在房梁上父亲僵首的腿,投井后母亲漂浮在水面散开的黑发……那些画面如同淬毒的匕首,深扎心底,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剧痛。
十西岁的清姬,不再是浅井家的大小姐,她像一件被剥离了灵魂的精美货物,在债主肮脏的手中被辗转、估价,最终被卖入吉原最顶级的销金窟——“琼楼。
鸨母藤原夫人保养得宜的手指,冰凉而有力,如同鉴赏一件新得的稀世瓷器,捏起她尖俏的下巴,迫使她抬起空洞的眼睛。
藤原夫人的目光锐利如刀,在她脸上逡巡,带着估价般的精准与冷酷。
“浅井清姬?
藤原夫人红唇微启,吐出的字句带着脂粉的香气和砒霜的寒意,“死了。
从今往后,你是‘朝颜’。
朝颜。
朝生暮死的花。
藤原夫人深谙此道。
越是脆弱易逝的美,越能勾起那些掌握着权势与财富的男人们一掷千金的征服欲。
看着美好的事物在掌心凋零,是他们扭曲快感的一部分。
一个承载着没落贵族血统、拥有绝世姿容且注定短暂凄凉的艺名,是藤原夫人精心炮制的致命诱饵。
于是,浅井清姬被彻底埋葬。
活下来的是“朝颜,“琼楼耗费巨资、倾注心血精心打磨的镇店之宝。
“雪见香阁成了她的囚笼,亦是她的舞台。
西壁糊着的金箔底纹唐纸在烛光下流转着奢靡的光晕。
她指尖拨弄着名贵的三味线,丝弦震颤,流淌出的音符不再是京都庭院里的清风明月,而是精心编织的、魅惑人心的网。
一曲《六段调》,技法精湛,情感空洞,却足以勾走座上豪客的魂魄,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奉上成箱的金判。
她是游郭不朽的传说,圣洁得不染尘埃,疏离得遥不可及。
她是“白鹤,被供奉在神龛,接受着欲望的香火。
唯有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,当最后一个醉醺醺的客人离开,当侍女阿菊也退下休息,“雪见只剩下无边的寂静和浓郁的熏香。
朝颜才会褪下所有伪装,赤足踩在冰凉光滑的榻榻米上,走到那面镶嵌着螺钿的漆黑妆镜前。
镜面冰冷,映出一张毫无瑕疵的脸,眉如远山,眸若寒星,唇似点朱。
她伸出纤细的手指,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专注,轻轻抚摸镜中倒影的轮廓。
指尖下的触感是冰冷的,镜中人美得惊心动魄,却也空洞得令人窒息。
指尖微微颤抖。
镜中那双曾经盛满京都春色、流转着灵慧光彩的眼眸,此刻只剩下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水。
那曾经的光,早己被这华美金丝笼一寸寸、无声无息地、温柔而残忍地勒灭。
剩下的,唯有一片精致的、冰冷的、令人绝望的空茫。
她抚摸的,是一具名为“朝颜的、美丽的躯壳,而那个叫清姬的灵魂,早己在踏入“琼楼的那一刻,就停止了呼吸。
妆台上,一支纯金的簪子在烛火下反射着冰冷的光,像一根勒紧她脖颈的金丝。
窗外,吉原的喧嚣隐隐传来,那是属于买醉、欲望与交易的永恒乐章。
门被轻轻拉开又合上,侍女阿菊小心翼翼地探头“朝颜小姐,山田少爷他们…还在等您回去续酒。
朝颜的指尖从冰冷的镜面上收回,瞬间,那精致的空茫重新覆盖了她的眼眸,如同戴上一副完美的面具。
她转身,吴服宽大的袖摆划过一个优雅的弧度,方才镜前那一丝脆弱的颤抖消失无踪,只剩下属于“白鹤的、无懈可击的疏离与温顺。
“知道了。
她的声音轻柔悦耳,听不出任何情绪。
阿菊退下。
朝颜深吸一口气,那浓郁的奇楠香此刻却让她胃里一阵翻腾。
山田少爷,那个仗着父辈权势、眼神粘腻如蛇的纨绔子弟,方才席间借着酒意,言语越发轻佻露骨,粗糙的手指更是几次试图触碰她的衣袖。
强压下心头的厌恶与窒息感,她需要一个短暂的逃离。
“更衣。
她淡淡地对空气说了一句,并非真的需要更衣,只是一个借口。
她需要一口真实的空气,哪怕是从后巷那扇破旧仓房的门缝里透进来的、带着霉味的空气。
她拉开“雪见通往内部走廊的门,没有走向更衣室的方向,而是脚步轻盈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急促,穿过回廊,走向“琼楼最偏僻、连接着后巷的那道小门。
身后,山田少爷粗嘎的笑声和同伴的奉承声隐隐传来,如同附骨之蛆。
她推开了那扇沉重的、平时鲜少开启的木门,门轴发出刺耳的“吱呀声,门外,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、弥漫着腐朽尘埃气息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