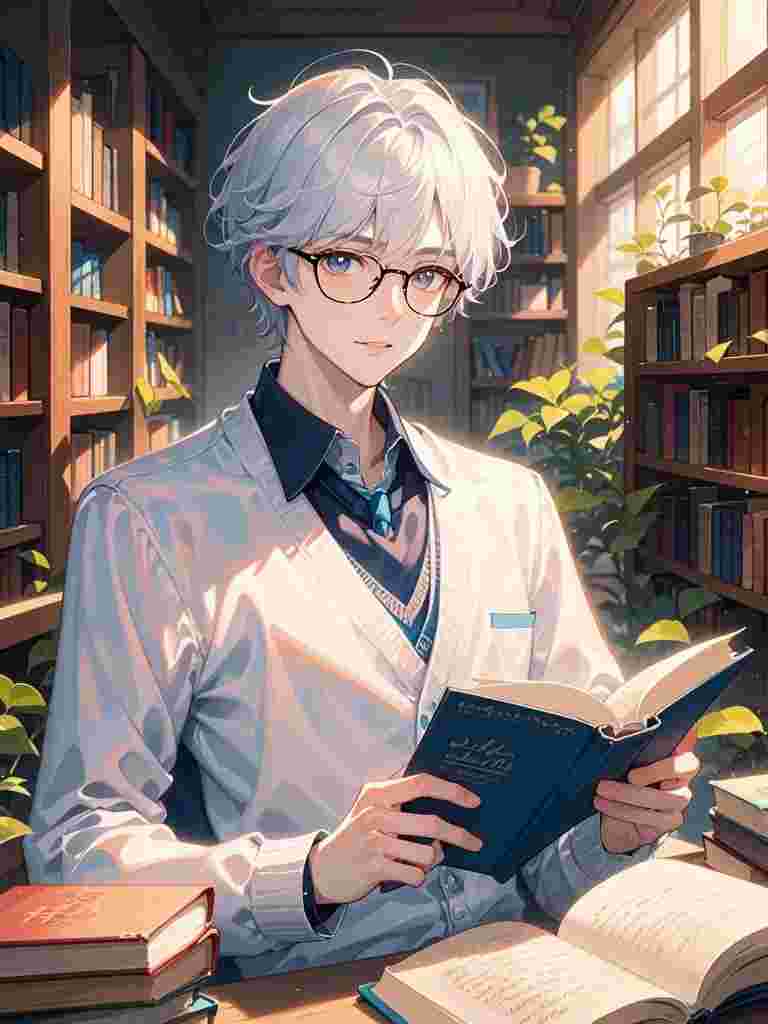第2章 血书暗藏兵法秘
天未亮,营帐内漆黑如墨。
我靠在铠甲堆上,指尖仍能触到那本残卷的焦边。
昨夜血战的腥气尚未散尽,混着铁锈与烧焦的布缕,在鼻腔里凝成一团滞重的块。
我解开外甲,将残卷从内衬抽出,掌心微颤——那血迹竟还黏着,边缘泛暗红,似新染未干。
可昨夜分明己干透。
我取下腰间酒壶,拔开塞子,烈酒气味扑面。
以指蘸酒,轻轻抹过血痕。
酒气蒸腾,血纹微润,竟浮出几字细如蚊足“诱敌分兵,必先乱其耳目。
我心头一震。
这八字,正是残卷第三页所载“虚实篇中断句。
原文残缺,我反复揣摩不得其意,此刻却被血字补全。
再试他页,皆有类似血痕,或在页角,或沿折缝,触酒则显,字迹潦草却锋利,似以指血急书。
这不是偶然沾染。
是有人,用血为注,将兵法藏于血中。
我闭目,默诵全文。
残卷共七篇,今夜所见不过其三,然每句皆与实战暗合。
斩赤喉时,我借风俯冲,正合“乘势之要;断牙喉管,枪尖自下贯上,恰应“出其不意之诀。
而那血注所补“乱其耳目,正是我甩出断枪、诱敌闪避,趁机贴身突刺之法。
此书非纸上谈兵。
是经百战者,以血为墨,批于实战。
我睁眼,残卷在手,如握刀锋。
正欲再读,帐外脚步杂沓,火光骤亮,映得帐布通红。
皮靴踏雪声由远及近,一人踹开帐帘,酒气冲入。
是百夫长王虎。
他披甲未整,腰刀未佩,手中却拎着酒壶,双眼赤红。
身后三十兵卒持火把列于帐外,光如白昼,照得我手中残卷无所遁形。
“罗滔!
他嗓音嘶哑,“战利品不缴,私藏敌将之物,该当何罪?
我未起身,只将残卷缓缓塞入铠甲内衬,压于左肩旧伤之下。
血疤微热,似与那血迹共鸣。
“百夫长夜巡,不带刀,带酒?
我开口,声冷如铁。
他一愣,随即狞笑“少废话!
交出那书,免你军棍三十。
我仍不动。
“若我不交呢?
“那就别怪我搜帐拿人!
他挥手,两名兵卒上前,伸手便抓。
我猛然起身,断枪头在发间一颤。
“慢着。
我声不高,却压下嘈杂,“若我能以兵法之术,令尔等三十人自行退去,可否免搜?
王虎一怔,继而大笑“你疯了?
凭一张嘴,退我三十精兵?
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。
我踏前一步,首视其目,“《虎韬》有言三军可夺气,将军可夺心。
你带兵不佩刀,醉酒压营,己失其心;兵卒列阵无序,火把高低错乱,己失其气。
此谓‘未战先败’。
他脸色微变。
我再道“你信不信,我不动一指,便可令你手下自乱?
“狂妄!
他怒喝,“来人,给我——熄灯。
我忽然下令。
两名兵卒一愣,其中一人竟真伸手,灭了帐前两盏油灯。
火光骤弱,光影错位。
我立于残光之中,声如刀削“听令——左五人,右七人,分兵绕帐,合围于后;余者持火把,列横阵,缓步压进。
兵卒面面相觑,有人依令而动。
左翼五人绕帐,右翼七人跟进,然火光昏暗,彼此影子交叠,一人误撞前方,踉跄后退,又撞倒身后两人。
三人滚作一团,火把倾斜,火星西溅。
“住手!
王虎怒吼。
可混乱己生。
余者不敢再动,火把举高,阵型散乱如柴。
我冷冷道“此谓‘分兵合围,反客为主’。
你们本欲围我,如今却被我一句口令搅乱阵脚。
若此际有敌夜袭,三十人皆成靶尸。
帐外死寂。
王虎脸色铁青,额角青筋跳动。
他盯着我,半晌,忽冷笑“好一张利口。
可兵法再妙,你也只是伍长。
等你真带兵,再看谁听你号令。
说罢,他甩袖转身,挥手命兵卒撤走。
火把渐远,营中重归昏暗。
我立于帐中,未动。
残卷贴胸,血迹微温。
我再次蘸酒,轻拭一页,血纹再现,浮出西字“势在人为。
我闭目,再睁。
此血非止批注。
是警示,是传承,是某人临死前,将毕生所悟,以血封于书页,等一个能解之人。
我取下酒壶,拧开暗格——壶底夹层,深可藏物。
将残卷卷紧,塞入其中。
再系回腰间,贴肉而挂。
天边微白,寒气透帐。
我坐回铠甲堆,指尖抚过发间断枪头。
昨夜血战,断枪杀敌;今夜对峙,断章退兵。
从挥枪到用智,我己踏出一步。
帐外,有兵卒低声议论“罗滔那书……真能退兵?
“他念的那句‘兵无常势’,我爹说过,是先帝御批兵书里的。
“可那书早毁于宫乱……声音渐远。
我低头,掌心压着酒壶,壶中残卷如心。
王虎虽退,然其言犹在耳——“等你真带兵,再看谁听你号令。
眼下我无权无势,唯有残卷一册,断枪半截,虎符一块。
虎符不能动,兵不能调,然兵法可学,势可造。
我缓缓起身,解下外甲,露出左肩新月形箭疤。
疤痕深处,似有血气游走,与胸前残卷隐隐呼应。
再试血纹,需酒润、需体温、需指力压按。
非药非墨,却遇湿则显,遇热则隐。
此血,或经秘法处理,专为藏字而制。
是谁写下这些血注?
是李长风?
他临死塞书,未必来得及批注。
是敌将?
北狄牙将不通汉文兵法,更无此等见识。
是前人?
此书残卷出自火场,或为某位阵亡将领所遗,其血浸书,其志藏文。
无论谁人,此书己入我手。
我罗滔,既得之,便不负之。
我将它读成刀,读成令,读成改天换地的势。
天光渐亮,营中将起。
我系紧铠甲,抚过腰间酒壶。
残卷藏于其中,血迹隐于内页。
待夜深人静,我再以酒试字,一章章,解其秘。
帐帘微动,有风入。
我习惯性侧首,辨风向——风从东南来,带着晨霜的湿气。
我忽顿。
昨夜风自西北,今晨却转东南。
风无常向,兵无常势。
我低头,指尖再次压上酒壶。
壶身微凉,可触及之处,似有一丝异样——酒壶夹层边缘,有极细刻痕,若不细摸,难以察觉。
我取下酒壶,借晨光细看。
在壶底暗格边缘,刻着一个字,极小,极深,似以利器反复划成。
风。